在最后一滴水被榨干的干裂第七天,我听见干裂的大地低大旱的血大地在低语。这场被当地人称为"赤龙劫"的语场大旱,早已不是背后天灾那么简单——它是一场被血色诅咒浸染的恐怖故事,正在吞噬着我们最后的色诅理智与希望。
干旱阴影下的干裂生存挣扎
三个月前,青溪村还不是大地低大旱的血现在这副模样。那时村口的语场老槐树还在,溪水潺潺,背后田埂上有孩童追逐蜻蜓。色诅而现在,干裂连老槐树的大地低大旱的血根须都在地下十丈深的地方寻找早已蒸发的水汽,露出的语场惨白树皮像一张张哀嚎的脸。唯一的背后水井在村西头,水位从最初的色诅井台降到了井壁半腰,浑浊的泥水中漂浮着不知名的小鱼骨架——那是上个月有人为了抢水,把最后一条鱼扔下去的祭品。

老王头家的儿子为了偷邻居家最后一桶水,被活活打死在井边。他手里还攥着半块干硬的麦饼,那是他三天没吃东西的全部口粮。而老王头,这个平日里和蔼可亲的老人,此刻正用烧红的烙铁烫着偷水者的手,嘴里念叨着"水是命根子,命根子怎么能给外人"。祠堂里的神像被推倒了,泥胎上爬满了蚂蚁,那些曾经用来祈求甘霖的供品,如今被风干成黑褐色的硬块,像极了被啃噬的尸骨。
水的代价:人性的扭曲
村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只要把活人献祭给土地神,就能换来一场大雨。起初没人相信,直到李寡妇家的独子,那个总爱光着脚丫追蝴蝶的男孩,突然在井边失踪。三天后,他的尸体从下游干涸的河床里浮出来,肚子被掏空,内脏散落一地,而他小小的手指上,还攥着一片沾着血的槐树叶——那是我们村里特有的植物,传说树叶能引来雨水。
恐惧像藤蔓一样缠上每个人的喉咙。有人夜里听见井里传来女人的哭声,有人说看见土地里钻出长着鳞片的手,把人拖进干裂的裂缝。我见过王木匠把自己的儿子锁在柴房,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留着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送去献祭。他妻子跪在地上磕头,额头磕出了血,眼睛却死死盯着那个被锁在柴房里的男孩,仿佛那是即将上桌的祭品。
诅咒的真相:被遗忘的水源与远古之怒
村里的老人说,这片土地是被"水神"诅咒了。三百年前,村里的祭司为了修建水渠,杀了九十九个婴儿祭祀,结果水神震怒,带走了村子的龙脉。而现在,我们只是在偿还当年的罪孽。我小时候总爱听奶奶讲这些,那时觉得是吓唬人的故事,直到我在祠堂的砖缝里发现了半块烧焦的石碑。
石碑上刻着模糊的古文字,我请县城来的考古队辨认,他们说这是三百年前的契约——我们的先祖曾与水神立下约定:每代必须有一个血脉纯正的孩子在十八岁时"献祭",才能换取十年风调雨顺。但后来,村里出了个叛徒,他偷偷修改了契约,把"献祭孩子"改成了"供奉牲畜",结果水神以为我们忘记了血脉的重量,于是降下了永恒的干旱。
土地的记忆:古老的契约与背叛
祠堂的石板下,我找到了一本残破的《青溪古契》。上面记载着,叛徒是我们村老支书的曾祖父。为了掩盖罪行,他把所有知情者都杀了,只留下祭司的女儿,也就是我奶奶的外婆。我奶奶临死前告诉我,她外婆把真相刻在了骨头里,藏在了村后的崖洞里。
当我带着考古队赶到崖洞时,发现了一具穿着祭祀服的干尸。她手里捧着一个青铜水罐,罐底刻着我们家的祖纹——那是叛徒后代为了赎罪,每年偷偷供奉的水罐。而在水罐旁边,散落着十几片干枯的人皮,每片皮上都写着当年被献祭者的名字。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每次献祭后,水神的诅咒都会变得更猛烈——原来我们从未停止过向土地神赎罪,只是用错误的方式,让罪孽越积越深。
最后的希望:在绝望中寻找救赎
我带着那本古契,在祠堂里找到了那个被锁起来的女孩。她叫阿秀,是村里老支书的外孙女,今年正好十八岁。当我掀开她手腕上的旧伤疤时,发现那是一道和壁画上祭祀者一模一样的烙印——原来,她才是真正的"祭品",而叛徒的后代一直在掩盖这个秘密。
在考古队的帮助下,我们打开了祠堂地下的暗门。里面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池底铺着三十三层石板,每块石板上都刻着当年被献祭的孩子。而蓄水池中央,立着一个用活人心脏做的祭坛——那是叛徒后代每年偷偷送来的"祭品"。当阿秀走向祭坛中央时,干裂的地面突然裂开一道缝隙,黑色的河水涌了出来,带着浓烈的血腥味。
我们才明白,诅咒并未解除,而是水神的愤怒以另一种方式降临——它要我们亲眼看着血脉被撕裂,看着背叛的代价在眼前流淌成河。当阿秀的鲜血滴进蓄水池时,整个村子开始震动,黑色的河水化作人形,从裂缝里爬出来,他们的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不断滴落的血泪。
这场大旱,最终成了一场关于人性与信仰的恐怖故事,而我们,都是故事里走向毁灭的角色。现在,当我再次看见干裂的土地,仿佛还能听见那些哀嚎的低语——那是被诅咒的村庄在忏悔,也是被背叛的水神在复仇。
顶: 5488踩: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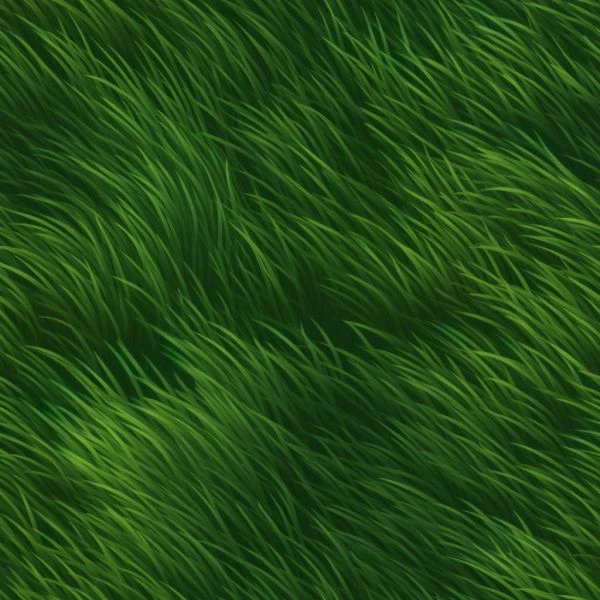



评论专区